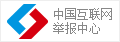高晓松:我喜欢过去的时代和现在的我
|
房子会伤害我和一切 B :宋柯开了个餐馆,你这么爱吃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开? G :我到现在什么都没开过。人一生能做的事很多,我还能当记者呢,我没准儿也能拍照片,我没准儿还能犯罪,我至少不会那么傻就让人给逮着了。能做很多事,但你不能都去做,我觉得凭我这么多年攒下的资源和人品,我也是可以做生意的,我就不做,我什么事都不做,因为我觉得没意思,我只干有意思的事儿。另外是我欲望特别弱。譬如说我想买房,那我就得想办法了,但我又不买房。 B :你不买房,全世界各地都在租房子住? G :租房子很好啊,想住哪儿就住哪儿,今儿看到这个就住这儿了,明儿看到那个就住那儿了,无非就是倒霉两天,每次搬家的时候都说:唉,要不买个房子吧,都麻烦死了。我一想到买房的后果,我就想着不要买了,因为房子会伤害我和一切。我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很稳定的生活结构里,但是一买房会破坏,因为你需要很多钱,当你需要很多钱的时候,你就想做点什么事,你想做点什么事的时候,你就想利用别人,你一想利用别人,你的整个的稳定的生活结构就破坏了。 B :你书里说不买房是受了你妈妈的影响,她曾经跟你说“生活不是只有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”。所以你们全家都是无房族么? G :我妈也没买过房。我妹也没买过房。我妹钱比我多多了,捐了很多小学等等,但从来没买过房。我妹妹在德国生活了很多年,现在回来了,以极简的方式生活,吃素,德国籍的孩子送到民工小学上学。我老婆是很爱穿衣服的,我妹的所有衣服都是我老婆的,穿我老婆不爱穿的。我妹妹很疯狂的,她一个人可以骑着摩托车穿越非洲。 B :听起来你们全家都很洒脱,你觉得你做过什么疯狂或者让自己骄傲的事? G :好像没有,对我来说一分钱不带去要饭那都不叫疯狂,这个事情我也做过,和家里人打赌,我想组乐队,他们不让,便想为难一下我。他们说你敢吗?你敢拿把琴就走吗?我说我敢,于是爸妈搜我身,把钱都搜光,给我买了张火车票去天津,说一礼拜后你再回来,如果你坚持下来,乐队的预算和资金立马就拨给你,因为组乐队要花很多钱。虽然我们家心疼我,只让我去了天津,爬也能爬回来,但真一分钱不带就上天津那也挺要命的。 B :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?后来打赌赢了么? G :大一。我记得我在天桥那边弹琴,一天下来就要到了 5 毛钱。然后花了 4 毛 7 买了盒烟,一口饭都没吃,当时 1 毛 5 可以买一方便面了,但是我有很多感慨,我得买盒烟。第二天,我想可能大学会比较喜欢这种事,就去天津大学卖唱,结果被人举报了,被学校保卫处抓起来了,说我是流氓。最后是被我们家领回去的,导致打赌失败。但是我们家的教育是特别好的,特别西式,虽然我失败了,饿得半死,但回到家就看到一大桌菜。从那以后到现在,20 多年过去了,没有人提过这件事,包括那一天,也没人提什么你打赌失败了,因为大家觉得你是一个男的,你心里肯定都明白了,那还提它干吗? B :那还蛮有趣的,在这种鼓励下,你应该会干出更多不靠谱的事。 G :我确实经常干这种一分钱没有就敢出门的事。我在欧洲也发生过这种事,浑身上下一分钱没有,卡也刷爆了,没存款,我从来就没有过存款。我买不了房子就是因为没存过钱。最后打电话给北京的哥们儿,说你先借我点钱买张机票,然后他给我订张机票,让我去国航在罗马的办事处去拿机票,于是我又蹭了各种车去了罗马,拿了机票。最后坐着免费的接驳车上了飞机,一看旁边坐着一个中国人。我高兴坏了,我就问他,你能借我点钱吗,回了中国到机场我就还你。他说行啊,然后我和他套近乎,因为人家借钱给我了,我问他你是干什么的呀?他说我是作曲的。我更高兴了,“你作曲的,你不认识我吗?”他说我不认识啊,我心里一下特别不高兴,作曲的居然还不认识我啊!然后我说我是高晓松,他说我没听说过,我气坏了,心想说出名字来都不认识,我就问他:“那您叫什么呀?”他说我叫瞿小松,我顿时消气了:“嗨,瞿老师啊,大师大师!我不算作曲的,我只是写歌的,您才是作曲的。” B :我感觉你现在的状态特别自在,是不是把很多东西一点点放下来,就越来越自在了? G :虽然我有很多毛病,但我从小有一个特别好的生活观念,这个观念到现在我都觉得一生有益:我从来不想自己要什么,我只想自己不要什么。我一直这么生活的,所以自在就是你把不要的东西都不要了,那就好了。 B :你怎么判断你自己不要了? G :我一直都觉得,这东西只要我不喜欢,那就不要了。不管它是什么,只要不要了就不要了。 B :对你老婆来说,你这样的岂不是挺没安全感?她也不知道,万一你什么时候突然不想要家庭了怎么办?而且你又没有存款,又不买房。对于一个在中国式教育下长大的女人来讲,你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男人。 G :但是我到 40 岁了,我对这个婚姻,对这个家庭,我是越来越依赖。因为你已经过了你男性能量的成长期,其实你是在往后退,所以你会越来越珍视这些东西。包括乡愁,我去了美国之后我就有了,包括孝顺,我以前也没有,因为他们太强了,所以感觉不到他们需要你孝顺,我现在也有了。我现在能跟妈妈、丈母娘都住在一起,丈母娘带着孩子跟着我跑,在美国大家都住在一起,回北京也是,丈母娘、老丈人、小姨子从我结婚起都跟我住在一起,共同生活很多年了。我还乐在其中,我原来是特别野的一独狼,看到我今天这样,我的那些朋友都傻了,徐静蕾说,你每顿饭都带着这么一大家子人啊。我说对啊,我说我告诉你,我现在不但不再是那头独狼了,我现在家里人少了我还受不了。我觉得怎么没人了?不热闹了,没意思。 B :这么复杂的关系,一大家子人在一起,你们都一直很和谐吗?从来没有矛盾吗? G :关键就是我脾气好,我只要脾气好,就都和谐了。你要是再有各种不平,那就完了。所以我说我是员外嘛,人家员外四房五房家里都能和谐相处,我这儿不就是俩老太太,一老婆,一孩子,还有什么不能的呢?老丈人关系也磨合得很好。 狂妄就是一种自私的集中体现 B :你做了这么多工作,拍电影写歌当主持人,为什么从来不考虑做个歌手? G :我就是坚决不想做歌手,我从小特别狂傲地长大,然后我觉得做歌手、做艺人在台上冲大家说“后面的观众你们好吗?”我觉得这样不好,我们家也接受不了,因为做幕后你就能成艺术家了,或者叫文艺工作者,于是就坚决不上台。等到后来呢,我觉得晚节不保也不好,别说年轻时候挺瘦的没上台,等老了弄一老胖子上去唱歌去了,算了还是坚持到底吧,宁可去做评委,就到现在都没唱。但我挺高兴偶尔能唱两个歌的,每场音乐会上我都会唱两个歌,《一叶知秋》和《恋恋风尘》。 B :你在台上的时候会不会回忆过去?当台上台下一起唱你过去写的那些作品的时候,你会有掉泪的冲动吗? G :我站在台上当主持人串场的时候没有,因为我说的时候会尽量让大家笑,我也不是一个苦情的人,我说的时候都是逗乐的,我和这哥们儿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,这哥们儿这姐们儿怎么怎么。但我确实会掉泪,当我站在旁边看到万人齐唱,泪雨滂沱,那种场景连宋柯这种铁了心肠的都哭了,我真的特别感动:你的人生是多么的有意义,你曾经抚慰过这么多人的心灵。 B :所以就是因为这个,就算你以前做过很多不靠谱不要脸的事情,你都可以原谅自己。 G :对。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原谅自己,一个人要是不能原谅自己,你就白成长了。我觉得成长的过程就是最后一定要能原谅自己。我现在就是原谅了自己,我连我自己都能原谅,我就能原谅所有人。总而言之,你总伤害过不少人,狂妄就是一种自私的集中体现,我曾经自私地生活过很多年,最终两件事会让你觉得特别平静:第一,你还了,该还的已经还了,你总要还,但是我觉得不同的还的方法,如果是以家人的寿命或是其他的代价去还,还不如去坐半年牢自己去还了挺好;再加上你原谅了自己和所有人,因为人生中不光是你觉得对不起别人,你还觉得很多人对不起你呢,包括家人等等,你还有好多讨厌的人呢,我现在都没有讨厌的人,我每次看到他们在微博打架我都兴奋不起来,要是过去我肯定直接就冲上去了,但我现在看着都觉得特别怪,为什么人们不能互相原谅呢?为什么就要这么难以理解?我现在就是特别不理解。 B :你会更喜欢 1988 年的高晓松还是现在的高晓松? G :我喜欢 1988 年除了高晓松以外的那些东西,那个时代,那是一个好时代,但我是好时代里的坏孩子。我喜欢现在的我,今天的时代真的是一个坏时代,我不是说中国,是全世界,美国也一样,非常沦丧,我现在成长成了一个好孩子。 |
版权声明
本内容由“太平洋时尚网“原创,未经允许,请勿擅自篡改、抄袭或转载。如有任何合作意向或疑问,请先与我们联系。











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0160号
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0160号